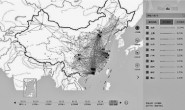(六)城市的合约性质
城市是由拥有分立的产权的人群聚集而成的。这些产权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合约构成密集的合约关系网。大量个体通过雇佣合约、购物合约、交通合约、税收合约、婚姻合约等多种多样的合约联系在一起。城市越密集,合约关系网也就越密。城市化的过程,是人口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也是大量拥有分立产权的个体之间编制的合约网变得更加密集的过程。怎样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地重新配置聚集而分立的产权?如果没有任何规划的限制,让城市的个体根据价格自发的签订合约来配置产权,其有效配置的前提是产权清楚且个体间签订合约面对的交易费用极低。然而,产权完全清楚与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并不存在,也就让政府通过行政力量配置资源,有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理由。但是,政府靠行政力量推行城市化,依然可能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且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没有机会成本和债务破产的制约,从而缺少纠错机制。产权不清晰或交易费用不为零,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唯一的替代选择,本文研究的蛟龙工业港的城市化过程,就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蛟龙工业港能在十年时间内快速的实现城市化,其基础并非行政权力,而是作为中心缔约人,与双流县政府、园区企业、农户、居民等订立了一系列合约。作为中心缔约人,蛟龙公司得以简化因人口聚集而变得越发复杂的合约关系网,降低了城市化的合约费用,从而得以按照自己的规划快速建设与发展城市。多方订约使蛟龙公司获得了规划权、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等建设与经营城市的重要权利,使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外部性问题内化为蛟龙公司经营土地的增值收益。
黄玉蛟作为蛟龙公司的企业家,成为支配这些合约的重要因素。蛟龙工业港从而成为企业和企业家主导城市化的案例。问题是,当蛟龙工业港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合约关系网变得更加复杂时,黄玉蛟及蛟龙公司作为中心缔约人,其订约成本是否会上升,以致于超过其能力限度?前文所述的,后期开发的城中村的拆迁困难等,开发建设的资金成本等,都将不断考验其对一个城市的经营与管理能力。正如每个企业家所能管理的公司规模有显著差异,不同企业家经营城市的才能也有差异。就作者所见,黄玉蛟有较强的前瞻力、合约创新能力、执行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其团队年轻且执行力高。黄玉蛟合约创新能力,对于在合约基础上建立的城市化至关重要。到底黄玉蛟及其团队能管理多大规模的城市,还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但是实践证明,以目前的蛟龙港的城市规模和密度,在民营城市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七)蛟龙社区
从上述讨论可见,蛟龙工业港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蛟龙公司作为中心缔约人,与双流县政府、农户、企业、租赁户形成的合约网的基础上。但蛟龙工业港还存在一个在这个合约体系之外的重要参与者,即蛟龙社区。
九江街道蛟龙社区由原九江镇万年村、大渡村、石桅村和泉水八队合并而成,辖区内面积3.9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013人,分为七个村民小组,辖区内共居住5万多人。蛟龙社区管辖蛟龙工业港的大部分区域,但并不与之完全重合。
与被征地后形成的社区不同,蛟龙社区依然保留了村庄的性质,但几乎没有集体资产。蛟龙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由蛟龙公司投资修建,蛟龙工业港提供交通协管,学校和医院也是民办,而蛟龙社区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城管、社保等服务。社区主要工作人员没有行政编制,经费来自于政府补贴。蛟龙工业港通过合约界定经济权利的同时,也将经济职能从原有的村庄剥离,从而使村庄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力相分离。蛟龙的城市运营是建立在合约之上,通过合约界定经济权利,而无法通过合约界定的产权则留给社区以行政权力配置。
四、总结
本文探讨了如下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否只有政府主导这一种模式?是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可以替代的其他道路?如果存在,其经济机制是什么?
蛟龙工业港是在集体土地上由民营企业建立并经营的城市。如果我们把城市分为国有城市与民营城市,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采用前一种模式,而蛟龙工业港则是后者的一种成功探索。蛟龙的实践表明,以下几个条件并非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土地财政、政府征地、政府规划、政府招商引资、政府供给不同用途的土地、政府以协议出让的方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土地储备的方式控制商业用地的供给、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并引导产业升级、政府高举大量债务来经营城市等。”
上述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模式,是在给定土地、规划等制度约束下的选择,依靠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合约来配置要素资源。这种模式在中国普遍存在,但并不代表政府主导是最有效率的模式。而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禁止集体土地入市,以及建设用地指标的计划配置。这使得最基层的村庄,难以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即使有建设用地,农民和企业也无法直接利用农村的土地建城。土地产权不合法,金融机构就不敢做抵押贷款。政府建城的模式,是在既有土地、规划、金融等制度安排约束下,地方政府不得已的行为选择。只要制度允许更大的弹性,就会出现更多样的城市化方式。
蛟龙工业港能在十年时间内快速的实现城市化,其基础并非行政权力,而是与双流县政府、园区企业、农户、居民等订立的一系列市场合约。蛟龙公司作为中心缔约人,通过与多方订约的方式,调动城市中分散的要素资源的产权。其中的核心是与双流政府签订的合约所界定给蛟龙公司的规划权与税收分成,以及蛟龙公司与农户、企业、居民的租赁合约。这些合约使蛟龙得以参照市场价格的变化,发挥黄玉蛟的企业家才能,分配土地等空间资源,将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外部性问题内化为蛟龙公司经营土地的租值收益。 蛟龙公司的实践表明,由企业自主规划,以签订市场合约而非行政征地的方式, 是可以在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快速实现城市化的。
当然,受制于现行制度的约束,蛟龙工业港的城市化模式尚存完善之处,其租赁合约、城中村拆迁、融资方式等也未必是最优的选择,而类似黄玉蛟的企业家也需要合适的选择机制。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地区试点开展类似的试点,改革土地制度,修改规划程序并予以留白,使优秀的企业家与公司得以建设与经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会有更多样的形态。
文/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本文选自《城市的合约性质:民营城市蛟龙工业港》
原文发表于汪丁丁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5辑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的民营城市为什么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