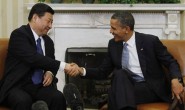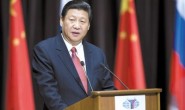是以,除2月的报告外,所谓的“许景澄言论”均来自金楷理的转述。然而另有史料证明,即使是2月的晤谈,也有金楷理在场。2月报告中虽只字未提金楷理,但随后不久,3月18日德外部高级参事官克莱孟脱(Klement)在其手稿中谈及此事:“驻柏林与圣彼得堡中国公使及使馆参赞金楷理(kreyer)于本年二月劝我们先直接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行谈判。”显然,拉度林与许景澄的对谈,是由金楷理担任翻译工作,居间传话。因此,是许景澄确有支持武力之意,还是金楷理在传达过程中扭曲原意,要打个问号。真相究竞为何?恐怕还要考问金楷理的个人背景,也要厘清晚清驻德使馆的具体外交运作。
金楷理是美籍德人,1839年出生于德国,青年时期随家人移居美国,1866年被美国浸信会差会派到中国。最初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与李风苞合译了多部德文军事书籍。后李风苞使德,调其前往柏林任使馆翻译,后升职为参赞。此后二十余年间,金楷理一直在中国驻柏林使馆供职,历经李风苞、许景澄、吕海寰、荫昌等数位驻德公使。因使馆中能通中德两国文字者只他一人,前后几任驻德公使都对他极为依赖。他曾因售卖假军火、勒索回扣,为德国政府不满。锡乐巴(德国铁路设计师,胶济铁路的主要设计者)曾在报告中称“使馆翻译金楷理博士从卖方勒索到订货总价的百分之七点五”,李鸿章也提醒过许景澄:“金楷理在德,声名甚恶,文卿(即洪钧,前任驻俄、德公使)深倚之,故不为外部所喜。”如此种种,侧面反映了金楷理的品性问题。
德国政府对金楷理的不喜,涉及当时海外军购的贪污、腐败及竞争。但使德方真正耿耿于怀的是其对外交的过度干预。一方面,晚清使外官员多为旧式知识分子,如前后出使德国的洪钧、许景澄都是翰林出身。根据清廷规制,出使大臣属于临时性的差使,设职之初便声明“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并未经过专业的选拔和培养。因此,大部分的出使官员既不精通外语,更不熟悉近代外交法则与技巧,交涉上就不得不依赖外籍参赞和翻译官,由外籍参赞代为交涉的现象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驻外使馆内的参赞与随员,人事权属于驻外公使。出使之前,由公使拟具一个名单,奏调出洋,任期结束又偕同公使回国。这个以公使为核心的团队,每数年一更换,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的有外交经验的系统。如此一来,长期留在使馆中处理具体事务的,反而是游离在公使团队之外的外籍参赞或翻译。以金楷理为例,二十余年的驻德使馆生涯,不仅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比较熟悉中德事务,也拥有较大的事权,“金楷理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占有重要的位置,像马格里博士在中国驻伦敦使馆一样。中国的外交官对后者也是过分依赖,所有的政府命令都经过他的手”。
巴兰德在1890年对许景澄倾诉过不满,要求将金楷理罢职:
巴云:“姑且不论德馆所用金楷理,我外部颇不谓然”。弟云:“从李大臣(即李凤苞,笔者注)起至我任内,到外部谈论公事,都是金楷理传话,直至那年曾侯到德,贵国外部告知不愿洋员传话,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带金楷理去,但使馆用此人,皆因频年买炮、造船,机器事理深奥,他却熟于翻译,且各大厂管事人等亦都与他相好,我所亲知”。巴色不悦,云:“如此仍要用他,恐于两国交涉有碍。”弟云:“我到贵国,亦要将话讲明,现在不令传话、不办公事,但令翻译、采办事件无甚妨碍。”
从巴兰德谈话可知,从李风苞开始,历任使臣到德外部交涉,皆由金楷理传话,德方不满已久。1886年曾纪泽访德时,德外部即已告知不愿由“洋员”即金楷理传话。后因金楷理对枪火、炮舰,尤其是铁甲舰的知识钻研甚深,又常年与德国伏尔铿厂等打交道,积累了相应的人脉和交情,使馆不得不继续使用此人。1890年巴兰德虽以于“交涉有碍”相挟,迫使许景澄承诺在柏林期间不让金楷理参与公事,但许景澄移驻圣彼得堡时,一切照旧,使馆事务仍由金楷理居间办理。
胶州湾事件之前,金楷理与拉度林在圣彼得堡过从甚密,数次私下晤谈,他怂恿德方使用武力,拉度林本人也持相同主张。由此种种情形似可推断,许景澄的“不当言论”,可能是拉度林的有意扭曲,也有可能是金楷理从中作祟。毕竟许景澄在柏林与德外交大臣马沙尔的对话中,从未出现类似主张,但在圣彼得堡的使馆中,却经由金楷理之口,有违常理地主张德国使用武力。
德外部从拉度林的报告中,敏锐地察觉到金楷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以金楷理僭越职权向许景澄发难,并最终改变了驻外使臣兼使俄、德的局面。1896年11月,许景澄上疏《请派德国专使片》,道出德国方面对于由参赞来接洽外务的不满:“德外部亦以使臣不常在德,仅由参赞接洽,隐怀不惬……彼国驻使曾向总理衙门述有政府要话不愿由俄都转电之说”。为了避免德方猜忌,许景澄建议此后俄、德分使驻守,让使臣能够专注于一国事务,同时杜绝由参赞代为办理外交的现象。清廷依议分别派遣黄遵宪为驻德公使,杨儒为驻俄公使。
对金楷理在中德外交中的影响以及传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巴兰德早有忠告:
像金楷理博士这样一个在使馆工作,熟练中德两国文字而又身居机要职位的人,不使他知道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再说一遍,要是公使发现德国外交部不以赤诚相见的话,——相见以诚是符合德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在目前是极为中国所重视的,——那末,他只能反躬自问。
金楷理居间传达的“许景澄言论”,与其他史料中许景澄言行之抵牾,印证了巴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长期遥指外交,对驻外使馆情形和金楷理品性都较为了解的李鸿章,在许景澄出使之初,也预见到了这一点:“竹使(许景澄字竹筼)洁己奉公,金楷理即不免浮言,则竹筼任内似亦未能罗罗清疏矣”。
四、余论
1896年11月,清廷在任命黄遵宪为驻德使臣后,海靖有意刁难,以黄遵宪在新加坡时贪污受贿为由拒绝。在澄清贪污后海靖仍坚持原见,在总署议及黄遵宪,“始终不肯接待,语极决绝,其他挟制诮讪语不可胜记”,实际意图在于重提港口一事。后再三以此事纠缠,翁同龢知其醉翁之意,叹道:“前使绅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难矣!”清廷最终不得不于1896年12月谕命许景澄为驻德使臣,此为德国第一任专使。
12月,海靖以同意增加关税为条件,再度提出以五十年租赁的方式割让一个储煤站,被李鸿章以“粗暴的态度拒绝”。威廉二世极为恼怒,声称“经过这样的拒绝后这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一次”,德外交部此时也基本放弃了继续交涉的努力,指令“马上坚决地作为最后一次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割让一个海军港的要求。如果这还不能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则最后必将干脆由陛下的军舰占领一个合适的地点,先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至此,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争持落下帷幕,最终就武力占领港口达成了一致。只不过在“和平的环境”下,德国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等待华人先给了我们一个报复的理由”。此后,德国政府甚少再与中国交涉,待至1897年威廉二世访问俄国,与俄皇密谈胶州湾问题之后,德国再无顾忌。11月巨野教案的发生,对德国而言,只不过是期盼已久的“口实”终于到来。
自1895年10月港口索求的提出,至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的事发,交涉已两年。此时距离国门洞开已半个世纪,浮沉于残苛世局的晚清外交,在探索与认知近代法则的过程中,有醒觉与转变,也有因循与巢臼,其中后者,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前车之鉴。胶州湾事件中,本应在频仍外患中积累经验,体察时势强弱的总署及其官员,难以全然抛却旧日虚骄,外交之道仍是表面以礼而隐持倨傲,大多拒绝正视变化的事态:或漫不经心,漠然置之,如德方多次交涉,对港口野心勃勃、势在必得,总署却认为“无须详为讨论”;或推托迁延,延宕处理,德方第一次提出索港后,总署久久不向恭、庆二邸禀告;或应付了事,处理模式机械僵化,交涉中多次以唯恐其他国家提出同样要求作为拒绝,这套简单雷同的说辞在晚清外交中屡见不鲜。如此种种,总归酿成晚清外交一大通病,即缺乏一个有效的外交应对机制,往往在事情初露端倪时,轻忽大意,不思未焚徙薪设法斡旋,待至事情爆发时唯有仓皇以对、被动因应。
其他交涉各方,亦各有局限与差错:李鸿章一味以以夷制夷的方法处理事端,过度迷信中俄互保。驻外公使许景澄,锐意于筹谋海防,但外交观念与方法落后陈旧,多为被动地传达讯息,少有积极作为。1895年11月德国曾有占领厦门附近的小金门海岛作为临时军港之议。当时德国兵船已集泊厦门,上海路透局发电报通知许景澄,然许景澄回复“数日后未有续音,想与上月电传中国与俄旅顺同一子虚”,将此事视为谣传。不仅对德国行动掉以轻心,更身在德国,竟对德国选址厦门的热议丝毫不知。交涉中活跃的各个外籍人员,暴露了晚清外交倚赖洋员充任中间交涉人的一大冗病。蒲安臣轻易代为允割中国利益,金楷理中饱私囊、僭越职权。最为李鸿章信任、被许景澄赞为“然心向华”的巴兰德、德璀琳,虽不否认其为中国周旋转圜的一面,但两者本质上都更忠实于德国国家利益。巴兰德极力陈说胶州湾是适宜的地点,对德国政府颇有影响;德璀琳左右逢源,在中国则为中国言事,在德国则为德国主张,他建议德国对中国“道义的取得”,看似是在为中国说情,实则仍是侵割利权,此举不过是为了“使中国政府产生一个德国正在支持它的印象”,如同德璀琳在李鸿章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忠实于中国的德国友人。将国之外交,轻率托付于他国之人,结局似已昭然若揭。
注释:略
作者:贾菁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