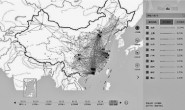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观察不仅一直影响着他的后续写作,而且最终导向了他对城市空间的乌托邦构想。在发表于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他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转向当时德国国内热议的“住宅短缺”现象 。针对普鲁东主义者们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所谓住宅短缺,和曼彻斯特的贫民窟一样,都是资本主义造就的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因此,住宅短缺问题应该被视作城乡关系这一中心问题的次生结果,或者说,这一短缺只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制度(necessary institution)。为了克服诸如贫民窟和住宅短缺这一类现象,必须首先找到办法消解城乡对立。
这个问题随后在《反杜林论》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分析。面对杜林所谓“城乡分割是社会之固有结构”的观点,恩格斯大加挞伐道:这两者之间的对抗性绝非内在于事物的性质之中,而只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外在表现 。也正因为此,杜林对城市空间的改良主义设想(根据技术和社会需求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并不能解决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问题。与之相对,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获得了别样的思想资源。两位乌托邦思想家都坚信,克服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建立在取消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而取消旧有劳动分工的首要前提就是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antithesis),代之以将人群以一千六百到三千不等分组,然后点状分配在大地上。这一系列乌托邦思想资源帮助恩格斯巩固了自年轻时便树立起的信念:城市终将消失,城市必须消失,继之以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分布。
通过借助这一革命的“反城市”脉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马润潮在1976年总结的“反城市主义”政策。那时的社会主义空间策略本质上是上述乌托邦构想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实践,而其中介则是斯大林 对城乡、工农和脑体三大差别的论述。尽管目前的政治议程已经与当时大相径庭,但是这种“反城市主义”理念似乎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城市观念和政策。为什么会如此?这个问题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个困惑,我想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反城市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和地理机制;第二,这一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以北京为例,我将在第三节中对第一个角度做详细探讨,而第二个角度则构成了第四节的主要内容。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反城市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和态度,可以与迥异的城市政策挂钩,我所关心的并非某项具体的城市政策如何延续至今,而是在不同的政策背后为何会耸立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观念。这一延续和断裂的辩证需要我们对历史地理过程作更为详细地讨论,而这也是我采纳谱系学的原因——“ 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为了离析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那些场景” 。
“反城市主义”的中国实践
“反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个维度的基础。在一方面,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特征不仅为民族精神添上了救亡图存的底色,而且也成为官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书写基础。在这些救亡图存的话语里,大城市(及其囊括的诸多租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提倡的重工业优先政策根本性地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成为制定城市和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为“反城市主义”态度和政策提供了根基。本节讨论将从一个简短的救亡图存史开始,力求将建国后的经济和城市(人口)政策放置在中国城市与现代性的历史脉络里。然后我将稍加论述斯大林模式对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和城市政策的主导性影响,并将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要素放入到北京城市规划的案例中去,通过经验性材料说明“反城市主义”态度在1950至1960年代的空间机制与社会效果,从而为接下来在第四节剖析城市人口调控的内在逻辑奠定基础。
通行的中国近代史论说均把鸦片战争视作“近代”的开端。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中国裹挟其中的时刻 ,也是“理性化进程从外部将中国人的生活带入普遍历史之中”的时刻。从那时起,如何救亡图存便成为整个民族的中心议题,并鲜明体现在种种对“现代”的追寻之中 。在陈映芳 看来,多重且动态的“现代化”目标自鸦片战争之后便成为驱动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自由、民主等理想。在这一根本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之中,相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城市和工业文明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后者因为其自身与现代性的内在勾连而成为承载着“现代”观念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是民族屈辱最为直接的表征——毕竟,帝国主义扩张在中国最鲜明的空间表达就是设立于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区 。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城市化的错综关联很快便激发出大相径庭的文化解读和城市观念。根据苏珊·曼 的综述,有三种对待城乡关系的态度盛行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第一种是乡土主义(nativism),以《中国家庭问题》的合著者易家钺为代表;借助顾炎武著作和当时大众文化中的反城市思想资源,他声称中国人的“民性”忌讳城市——作为农业人口,我们的历史和情感全部都寄托在乡土之上。第二种是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以董汝舟及陈子诚为代表;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资源,他们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快速城市化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长足进展)以及城市中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制度结构等议题上,并借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对“真民治”的呼吁,强调城市的顺利转型将足以造就新的文化渊薮和乡村枢纽。第三种则是乐观主义(positivism),这一派观点集中反映在吴景超193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之中。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是超越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一步,并将有望由此加入英国引领的社会进化历程之中;发达的城市和交通通讯设施不仅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而且最终能够帮助国民摆脱对饥饿的恐惧和对小农经济的物质与精神依赖 。
对待城市的迥异且彷徨的态度事实上反映了追寻“现代”的中国人的一种怀疑精神(ethos)。在这里,对“现代”的追寻本身内蕴着对“现代”的质疑。借用汪晖 的术语,这体现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这一语境与追寻“现代”的终极目标一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历史条件,并最终造就了种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受半殖民地经历影响的民族精神及其城市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反城市态度交汇并合流,然后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过程(尤其是其中的乌托邦实践)而深刻塑造了我们的城市体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市观念首先是历史性地生成的空间再现,其次才是受政策指令影响并服务于这些政策的空间机制。
具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农村逐渐被开拓为革命实践的前沿地带,“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取得主导地位 ,并成为建立新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和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一起,助长了一种将革命的乡村与保守反动的城市相对立的观点,这为新政权(及其领导层)的“反城市”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也构成了接下来“上山下乡”等“反城市”政治运动的一个乡愁性起点。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真正让“反城市主义”深入政治经济实践的是从苏联舶来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以“一五”计划及其中作为核心的苏联援建项目为标志,中国人迅速接受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一种时空间观念,并且模仿苏联,将重工业迅速发展视作走向“现代”的根本途径 。置身于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里,城市的属性和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城市与革命如何联结是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一个被热烈争论的话题。苏联的革命者们深受前述恩格斯之乌托邦观念的影响,坚信社会主义城市在物质形态和社会秩序上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而且城乡之间的差别一定会被消灭,但是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陷入了分歧。根据阿纳托利·柯普 的记述,苏联当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分裂成“城市主义”(urbanists)和“去城市主义”(de-urbanists)两个派别。“城市主义”者建议在城市中大规模兴建有充足交流和休憩空间的高层公社大楼(communal houses),这些每幢能够容纳五千居民的建筑本身可以构成城市空间的中心节点,核心和边缘的区分在这里也便无效了。“去城市主义”者们则走得更远,他们遵循着恩格斯的教诲,计划根据资源布局、工业基地建设和交通设施的发展将住宅平均地点缀在整个国土上,从而使人口回归自然,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与去城市化、中心与去中心、固定与移动之间的对立。当然,这两种乌托邦都没能变成现实。1930年5月,苏共中央做出最终裁决:“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只有把资源最大限度地应用在迅速工业化上才能够为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创造物质基础。这些有害的乌托邦方案一旦实施,必将导致资金的浪费并打乱我们对生活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
苏共中央的这一指令不仅表明了重工业优先方针的确立,而且也标志着城市空间在政治纲领中的地位被彻底降格。在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眼里,城市不再如恩格斯所述是取消劳动分工、克服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而是沿着一个新的脉络展开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容器——如此才足以构成最终解决城乡对立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这一近期任务和远期目标的区分具体地表达在了城市规划的官方定位上: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是将经济计划部门的决策给落实在图纸和大地上 。就这样,城市规划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被取消,成为服务于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类“后勤”部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变换了观察和使用城市的视角,但是不变的是对城市本身的漫不经心与排斥态度。毕竟,工业发展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树立起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与引进重工业优先方针同步,新中国也很快将苏联的这种城市观念和实践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的社论,其中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城市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最重要最基本的乃是工业……因此,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速度必然要由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来决定,这个客观规律是决定我国城市建设方针必须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根本原因” 。这一体现了苏联影响的城建方针随后迅速与“一五”计划同时应用到实践之中,指导了重点工业城市的新建和扩建以及一般城市的“维护”工作 。为了使资源和资本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在生产过程之中,城市只被视作承载资本积累和循环以实现工业化目标的物质载体。因此,城市建成环境(包括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等)被归入为非生产性领域,并陷入长期投资不足的窘境 。这一系列措施相叠加,最终形成了高工业化速度和低城市化水平并存的局面 。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城市人口调控的逻辑:反城市主义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