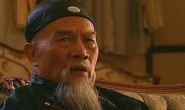能够印证上述规律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南宋中期以后,皇帝屡屡冠冕堂皇地颁布的减免税赋的诏令;但是对于这类政令,各地的官吏们不仅丝毫不必理睬,反而倒行逆施地发明出五花八门的办法,用以增设赋税的名目、私立征税的关卡,于是商税的征收不仅对于商贩、而且对于一切平民来说,都成了赤裸裸的抢劫:
当是时,虽宽大之旨屡颁、关市之征迭放,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验。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贸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栏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与斯民相刃相劘,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
这里,不仅是赋税制度成了直接屠戮百姓的“法场”已经足以令人惊诧不已,而且“贪吏并缘,苛取百出”这种机制所显露出来的,更是层层蔓生的专制权力结构必定导致无穷税弊(“其弊犹不可胜言”)这样一种铁律。
第三,非法加征的税额和税目不断合法化,成为了赋役制度沿革发展的基本走势;并由此而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保证了皇权不断专制化的趋向得到了合法化的确认。因为早如唐代政治家陆贽、南宋杨万里、李心传等许多人都曾痛心疾首地揭示了这一规律,所以我们称之为“陆贽·杨万里定律”。
上文指出,编户齐民头上的赋役负担,是随着皇权专制性在王朝中期以后的必然膨胀、以及官吏阶层自上而下的蔓生扩展而不断激增的。通过这样的势态,“不断加征赋役”也就具有了涵盖了皇权社会整个时间和空间序列的趋势。不过,如果加征赋役仅仅是权势者一种非制度化的欲求,那么其效用就终归是很有限的,那么此种有限性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被完全压倒的呢?我们看到,其方式就是“非法加征赋役不断合法化” 的过程。
非常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要支撑的,是一个体系庞大、功能高度完备发达的权力和行政制度,所以在上述两大加赋律的驱使下,它可以不断发明出无数的名目以作为加征赋役的理由。于是我们就看到:各种非法名目下苛捐杂税、征派劳役的日增一日,成为了专制权力制度延续生命的基本动能。然而百姓赋役负担的无限增加、各级官吏横索之下的苛捐杂税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税种和税额的主要部分(即后来顾炎武概括的“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这一趋势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出于维护制度安全的需要,王朝中具有改革眼光和能力的政治家则力图以归并赋役种类、简化征收过程为内容而建立新的赋役体制。新的赋役体制一方面不能不承认权力阶层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对已成事实的加征加派给予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希望以“并赋简征”的办法来限制加征加派的无限膨胀。于是每一次的赋役改革,就成了对以往加征加派合法性的事实上追认;而其一时的并赋简征,又成为了下一轮加征加派的起点。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定势:改革并减之后的赋税体制,总是要包涵以往非法加征的税种和税额;而并赋简征的新税制最终还是不能阻挡统治权力加征加派的趋势及其积弊的日甚一日,于是又要酝酿下一次的并赋简征的财政改革。
以“租庸调制”改为“两税制”为例,这次著名改革的重要起因,就是在租庸调制时代五花八门的加征加派已经实在无法遏制:
建中元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曰:“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输月送,无有休息。”
苛捐杂税多达数百种,可见其对制度安全的威胁之大、以及改制的迫在眉睫。然而改行“两税制”以后不久,非法加征却不仅卷土重来,而且在发明出五花八门的加征借口以欺世盗名上,尤其更上层楼34。所以陆贽《论“两税”七弊》中指出:
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宣索”、“进奉”之类,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又复并存,此则人益困穷。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税制改革之初曾经三令五申的“两税”之外不得再妄自加派的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二《重赋》中就详细描写了这种情况: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置绢未成疋,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百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令人惊叹的是:杨炎“两税制”的实施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而据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序》中自述,他的这组诗写于“贞元、元和之际”(公元804年前后),也就是说前距“两税制”的启动不过短短的二十几年,可是“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的法令已经是恍如隔世了!况且官员们除了如白居易所描写的那样以巨额的进奉取悦皇权、钻营升迁之外,他们更直接从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派中攫取巨大的私利,比如李翱奏称:施行“两税”之后,各地节度使又假借向朝廷“进献”之名加派赋税,其所得之中只有三分之一用来应付“进献”、而三分之二都装进了这些地方大员的私囊,于是使得“(百姓)父子、夫妇不能相养。”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顺便了解到传统社会中许多初衷在于除弊利民的财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实施的结果反倒南辕北辙的原因:正是因为在这种政治构架中,专制权力之利欲的恶膨胀最终是无法抑制的,所以历代一切改革方案中良好的设计(比如“两税制”方案中规定:每一项税额在征收之前都要经中央财政计算审核其是否合理、国家财政的支出额度要根据以往财政收入的额度而核准,等等38),都注定将成为泡影。这种定势之下,人们也就只能越来越放弃对改革的希望,转而幻想以“复旧”的方式回复到权力专制性尚未充分膨胀时代的境遇中。例如白居易列举实施“两税制”的种种弊端以后,满心希望能够重新实行贞观年间的“租庸调”制度:
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佣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佣法,令如贞观年。
政治哲学和经济理念的这种幼稚性,当然也是中国皇权“制度创造”的重要结果之一。
由于上述制度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至宋代的数次税制改革,更是在将以往的非法加征变为了合法税种的同时,又开启了种种新的非法加征税目。于是经过这样多次改革之后,百姓头上每项税役的征收额度已经是其承受能力的十倍以上,即李心传总结的:
予尝谓之: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已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催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矣;设有一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谷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四川路有“给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也。谷米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焉,是谷粟之征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输之,盖用其十矣,民力安得不困乎!
杨万里也曾痛陈改革税制最终反而促进了加征加派的事实,将他的奏札译成今天容易理解的现代汉语,其意思是这样的:
百姓以缴纳货币来代替以往要对衙门承担的劳役,这是本朝王安石推行“免役制”改革的原则;但是原来的劳役额度是根据该民户占用田亩的数目确定的,所以“免役钱”最初的数量因为与该户土地的数额相挂钩而终归有限。但是当“免役”税推行以后,它很快就脱离了与民户土地数量的关联而成为了单独的税种,所以在这个税种的名义之下而巧立的加征加派也就没有了限制,于是到现在,每年在这个税种上的加征,比当初立项之时的税额就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又比如朝廷在常设税目之外,加征了佐助执行临时任务之军旅的特别税,因为此军旅的统帅是由“经制使”担任,所以该项特别税就被称为“经制钱”。可是到后来,此军旅的编制已经撤消了,但是“经制钱”却并入了法定常设税种之中,成了百姓永久的负担。“总制钱”这个税种的设立也是如此:到如今,虽然“总制军”的建制早已撤消了,但是“总制钱”这项原本的特别税,反倒成了朝廷法定的常设税种之一而强迫百姓永远地缴纳下去。
再加上制定这些税种之初,百姓负担的税额只是粟若干斛、帛若干匹而已;但是沿革至今,其征收额度已经是:粟一倍于当初、帛几倍于当初了。除此之外,又生出“月樁”、“板帐”等等名目繁多的杂税,于是今天百姓的负担,已经不知道是本朝初期的多少倍,更不知道是汉唐时的多少倍了。况且这里举出的,仅是我所知道的东南地区的情况,至于我所不知道的蜀地赋税中各种无名税种之繁多,就更是无法列举的了。
我们知道,以各种临时性政举的名目加派新税,而该项政举裁撤以后,相应的税种却固化了下来,这种情况早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十分突出的,即如上引白居易《赠友》中所说:“兵兴一变(税)法,兵息遂不还”;而至宋代,这种方法更成了增加聚敛的不二法门,比较著名的例子比如:由于岳飞帅部进剿洞庭湖杨么造反军所需军费浩大,所以朝廷下令由户部加派赋税以为供给,但是当杨么被剿灭而岳飞军也撤离湖南之后,此项加派却依然征收不辍,致使“百姓狼顾,熟保其生!”。
再比如,“折帛”这项加派税目的设立,本是因为兵事频繁而导致军需纺织品价格暴增之后,而朝廷无力支应这项巨额花费,只好硬是生出“折帛”这加税名目以作弥补。但是当后来绢帛的市价早已大跌之后,这项加征并不取消,于是以“折帛”名义而搜刮来的资财如果真的用来购置绢帛,那么购买力已经是实际所需的三倍以上了。再者,当初全年只是加征一次“夏税折帛”(即作为夏税的附加税征收),但是到了后来,又在“和买”税的税目之下加上了“和买折帛”。这样一来,不仅征收了双倍的“折帛”税;而且“和买”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毫无道理的加征税目,现在非但不予撤销,反而在此加征税目下面又孽生出一项“其事无名,其取无义”的新税目——可见赋税加派的漫涨无际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宋代加派赋税的这种恶性膨胀趋势直接导致了王朝中后期的深刻危机;并且由于皇权社会的制税法理延续,直到明代仍然是经常沿用此法而增设新的税种。所以,如果通观历代赋税史就不难看到,正是通过上述不断地将加征加派、苛捐杂税归并入常设税制的方式和过程,皇权对编户齐民横征暴敛的日甚一日,才具备了制度化的强劲动力和“合法化”的必要程序,从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特征。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评论者对历代税制改革中将“力役”折变为货币税的举措(如宋代的“免役法”、明代“一条鞭法”等)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举有助于使劳动者从人身控制型的劳役关系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环境下,更促进了劳动雇用关系等等具有近代意义的生产方式之形成。
然而实际上,如果人们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切税制改革,其结果都只能是在专制皇权网络所构筑的制度平台上呈现出来、因而万难逃脱统治者以滥税牟私的铁律,那么评价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北宋仁宗时就曾大行过百姓出资、官府出面,顾人承揽原来由百姓轮流承应的劳役,这项赋税改革遂被称为“免役”、以其名义集纳到官府的钱称为“免役钱”。但是其施行的结果,却依旧是借此类改革税制而新生出一项盘剥百姓的名目,所以元代马端临就总结说:
时有王逵者,唯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馀,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产不能偿所负。……按,“役钱”之说,始于此,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及得钱,则以给他用,而役如故,其弊由来久矣!
可见,这类在七百年前就早已被有见识的制度学家完全识破的障眼法,如果在今天反倒博得长久的喝彩,那就真应该让人汗颜了。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古代的税制改革为什么总是越改越多?